公元2025年4月7日 夏曆乙巳三月初十
◉本期目錄
| ◼︎【編輯小語】活化經典 | 編輯部✍︎ |
| ◼︎【奉元活動】「毓老師逝世十四週年紀念會」側記 | 鄧力丰 |
| ◼︎【奉元問學之一】孟子的環境生態觀詮釋之一 | 潘朝陽 |
| ◼︎【奉元問學之二】三國雜談:論曹操 | 尹建維 |
| ◼︎【奉元問學之三】王船山《讀四書大全說》「致中和」 在「人道自立」的「日生日成」 | 陳有志 |
| ◼︎【公告事項之一】〔開課預告〕趙中偉老師: 乾坤六子,一索得男——「乾坤六子卦」解析 | 秘書處 |
| ◼︎【公告事項之二】四月行事曆 | 秘書處 |
【編輯小語】活化經典
文/編輯部
節氣清明,所謂「氣清景明,萬物皆顯」,奉元書院的春季課程(課程介紹)已進行了三分之一。週四晚間趙中偉老師的〖乾坤六子,一索得男——「乾坤六子卦」解析〗(課程介紹)即將要開課囉!有興趣的朋友,趕快來報名喔!如您對課程有任何建議或問題,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繫!更歡迎加入奉元書院官方 Line 帳號,只要在對話框輸入關鍵字(比如:「課程」、「行事曆」、「電子報」或 想要查詢的課程名稱、講師姓名等等)就可以找到想要的資訊喔!(加奉元書院官方Line為好友請按我)歡迎多加利用!
本期文章都跟活化經典有關。《中庸》強調「君子而時中」,就是主張根據時勢調整實踐方式,而非僵化守舊。《孟子‧梁惠王上》提出: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
代表處事需權衡變化,孟子也稱讚孔子為:
聖之時者也。(《孟子‧萬章下》)
這些經典的智慧之語,都在說明。弘揚傳統文化,需要有繼承更需要有創新,以現代人能夠接受的形式或語言,來傳達經典的道理與智慧。如此,才能「生生不息」!
想知道「毓老師逝世十四週年紀念會」都有哪些精彩瞬間嗎?請見:
〈「毓老師逝世十四週年紀念會」側記〉
你知道孟子的「王道仁政」思想與現代的「生態保育」觀念有何相通之處嗎?歡迎閱讀:
〈孟子的環境生態觀詮釋之一〉
你知道三國時的曹操到底是不是奸雄呢?請參見:
〈三國雜談:論曹操〉
你知道王船山對朱子四書學理的繼承與發揚為何呢?請參閱:
〈王船山《讀四書大全說》「致中和」在「人道自立」的「日生日成」〉
最後,編輯部亦誠摯地歡迎同門先進與各界同道友人,能夠共襄盛舉,提供個人無論是讀書、教學、工作、生活上的感懷,或是經典智慧應用的心得,在奉元電子報的園地中「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奉元活動】「毓老師逝世十四週年紀念會」側記
文/鄧力丰
圖/吳其諭
二〇二五年為 毓老師逝世十四週年,中華奉元學會於三月二十三日於奉元學會舉辦紀念會,由馬康莊常務理事帶領奉元同門,懷持對夏學不滅的熱情,與對 毓老師的崇仰、敬重以及懷念,以簡單而莊重的儀式進行祭拜,對遠去的老師表達無盡的懷念,並堅持著 毓老師所說:「以夏學奧質,尋拯世真文。」的目標,持續前進、展望未來。
下午二時,由司儀鄧力丰進行開場,並說明紀念會流程以及祭拜儀式進行流程,而後由馬康莊常務理事代潘朝陽理事長為主祭者,進行 毓老師祭拜儀式。



緊接著由馬康莊學長代替潘朝陽理事長進行致詞,馬學長以二〇一四年 毓老師逝世前十日,日本核電廠發生爆炸為引子,並根據中俄元首聚會所提出之「百年之大變局」,又引俄烏戰爭導致全球供應鏈斷裂、歐美關係出現裂痕、嚴重通貨膨脹、AI 的出現與對生活方方面面之影響,期許奉元同門後進可以準備好自身以因應此等變局。

二時四十分,由 毓老師親炙弟子,同時也是經典創新工作坊創辦人的張憶里學長進行專題演講,為大家帶來 AI 時代我們應該有的準備,同時引用 OpenAI 執行長所說的,在 AI 時代需要具備的技能,點出經典創新本身即具有AI無法比擬、無法取代的人性素養。並將《易經》所帶有的聯想思維系統與生成式 AI 進行比較,凸顯出《易經》以及夏學經典所帶有的獨特性。同時也引進了經典創新工作坊自行開發的桌遊《字字珠璣》以及《易想天開》,邀請熊羿秘書長,說明透過中華文字造字邏輯以及《易經》的系統思維,足以培養我們能在 AI 時代立足的能力以及優勢。


接下來是由白培霖學長帶來的奉元出版新書發表計劃。自上次開會以來,發表了林世奇學長整理的《毓老師講中庸》,而接下來將會出版的是《詩經》筆記,接著也會繼續出版《禮記》以及《尚書》的筆記,而今年上半年,也計劃出一套奉元同門林明進老師的書籍。
另外,白培霖學長也提到,奉元出版一直致力於整理並出版 毓老師講述經典時所留下來的筆記,因此也鼓勵各位奉元同門、 毓老師親炙弟子,如若有筆記,或是知道哪位學長姐有筆記的,歡迎聯絡奉元出版,奉元出版將親自聯繫,以期將 毓老師對經典的講述進行更加完整的留存、整理與出版。

接著是臺大奉元社報告,由奉元社社長鄧力丰帶來本學期社團活動之規劃如下:
一、邀請社團內研究所上榜學長進行研究所備考心得分享。
二、針對臺大、師大、成大、政大四校之研究所思想史考題進行讀書會。
三、邀請臺大中文系教授徐聖心進行《莊子》篇章講解。
四、以傳統中華燈謎、謎格、題材等等為主題進行讀書分享會。

最後一個環節,由馬康莊學長主持,邀請奉元同門學長姐進行分享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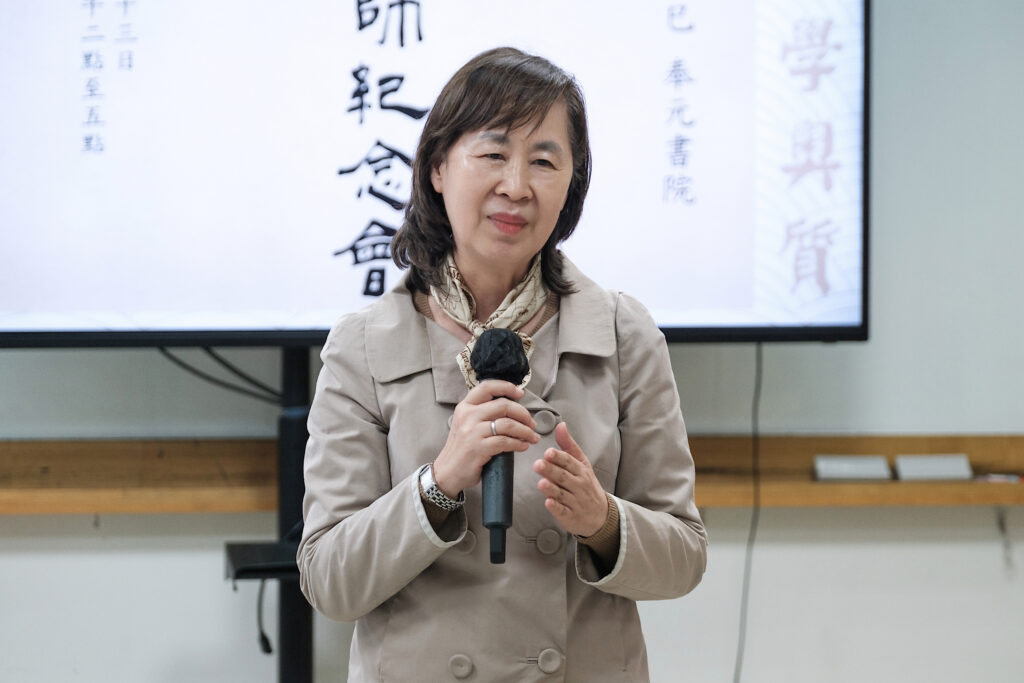

-全文完-
【奉元問學之一】孟子的環境生態觀詮釋之一
文/潘朝陽
一
中國「儒」、「道」、「陰陽」、「五行」各家都有豐富的「環境生態觀」。孔子已經在《論語》和《易傳‧子曰條》裏面,表達了他重視並且理解環境生態,且亦了解環境生態的結構、內容對於政經文明的影響。在孔孟荀先秦大儒的思想、學問中,其「環境生態觀」還沒有摻入「陰陽說」、「五行說」。具有淵源流長的「陰陽五行氣論」,影響了戰國末期的「易傳儒家學派」,而「陰陽」和「五行」之論也形成《呂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等秦漢時代的雜揉儒、道學理的著作。兩漢經學已是把「陰陽五行論」組入到儒家學術之中的漢儒之特性了,此與孔孟荀、《中庸》、《大學》等先秦傳統純正儒學大有不同。追溯儒家的原始性格,是必須的。
二
本文擇孟子之說來詮釋他的環境生態觀。〈梁惠王篇‧第三〉,孟子對梁惠王說: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這一章孟子對梁惠王問政的回應是千古以來最重要的儒家的王道仁政觀念。此文表達的宗旨乃是:孟子之王道仁政觀是實證性的政治學理;孟子不是玄學者、形上哲學家;玄學和形上學皆以抽象思維來建立政治學理及其意識形態;孟子是依具體實證的方式而從實學實務實政來建立他的儒家王道仁政。此段敘論有曰「王道之始」。然則,孟子之所謂「王道之仁政」,是有其開端或基礎的,此「王道之始」並不是意識形態、不是主觀的精神信仰,而是立基於土地與人之間的實務,是人地關係的自然環境和自然生態的和諧永續的運用,政治須從土地生產的生態永續起始。孟子提醒梁惠王,人文進入環境生態的正確的方式是「時」之把握和操作,他一開始就說「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人民進行耕作,最重要的關鍵是必須依四季循環規律而進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能如此循步漸進,依規律而行,則必有穀類的豐收,而糧食也就充沛,國人也就不會饑饉。同理,孟子告訴梁惠王,魏國的湖泊池塘,須禁絕數罟進入,如此,魚鱉等水產就能食不完;什麼是「數罟」?朱子說:「數,密也;罟,網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其實就是禁止密不透水的漁網下去池塘湖泊中把魚蝦一網打盡,這是生態環境永續的保育政策,人民就有魚類蛋白質營養來維持體力;斧頭刀子也須依時節之規律進入山林中伐木,材木就可永續而不會枯竭。基於上言,孟子提出了:農時不可違反四季循環規律、水產生態必須立法維護其水生物的永續生生以及人們必須依時節而入山中伐林取材,禁止對山林的濫墾濫伐。孟子於此表現了先秦儒家進步的、科學的環境生態保育論,而且,由此也看出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這個體系的儒家的基本政治觀念,為政之道,是從土地資源的運用、培育和取用出發,「生態永續論」的經濟學,是成功政治的必備。以孟子的話語,此即「王道之始」,它如何?就是:
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三
孟子接著又曰: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支持並且主張「井田制度」,《孟子》一書,是先秦很重視並且說明「井田制度」的經典。井田的政經制度是周代存在通行的一套土地經營制度,但由於春秋戰國的禮崩樂壞,「周文」不惟是上層結構衰敗,連下層的土地結構和組織也已頹毀,法家商君就是主張且推行廢井田開阡陌的政治家,但孟子的主張「周文禮樂」之土地制度,乃有其養民愛民之仁政的用義,上引此章句是孟子立基於「井田制度」而提出來的合乎環境生態永續經營的一套王道觀點。在此敘說中,有兩個基本的土地面積,一是五畝,一是百畝;兩者皆是孟子指出的「井田土地耕作制度」的一個農夫擁有的土地單位;五畝是其農宅,百畝是其耕地。「井田耕地制」是劃農地為「井」字形,以八個農家為一個井田中的耕作戶,每一農戶有百畝私田,而八家共同耕作中央的百畝公田,私田收穫歸己,公田收穫歸給公社。而在「井田制」中集聚形成的鄉社,則由政府設立學校來教育農村中的農民子弟。
孟子說明的農夫之宅如何?即「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每戶農宅的面積是五畝,其中當然有數口組成的一家人(孟子在對齊宣王論政時說是八口之家)居住的屋舍,可以避免風雨寒冷,得以安適居住;在其旁種植桑樹林,養蠶縲絲織布,所以五十歲以上的長者可以有帛衣穿著;而又在屋舍旁蓋有家禽家畜的棚舍,豢養雞豬狗等,讓禽畜皆可依時序而得以繁殖,這樣七十歲老者都可以吃到肉類,增加蛋白質、脂肪等養份來保健。孟子提出來的是「井田農業制」中,每家農戶基本環境生態中的維生之永續經營。
進一步,孟子就提到百畝之田,這就是「井田耕作制」中的八塊私田和一塊公田的基本面積。一農戶自耕百畝私田,八戶共耕百畝公田,皆必須不妨礙他們依據農時規律而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如此數口之農家都可以溫飽而不饑饉,公田也有收入而公社亦有公糧。這亦是合乎環境生態的生生永續規律的觀念而具備的農耕倫理,孟子表現了十分進步、科學的生態農業思想。
然而,孟子的王道仁政觀是承接孔子主張的富之之後而須教之的既富且教的思想,因為人若富足而卻無教化,則必如禽獸,因此,在國家的公社之中,需以公款設立學校來進行人民百姓的德教,此即孟子所言「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孟子主張的國民教育是五倫之德教,其中以「孝悌」之教養為核心。這是人文道德倫理得以永續剛健敦厚而發展的根本,也就是人民的經濟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則其人文道德倫理之教養也才能得其生生之德化,自然生態永續,人文生態和道德生態也才能永續。
因此,孟子告訴梁惠王: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如此而為政,這就必能實現王道仁政,何止魏國,甚至能依此而「王天下」。
四
中國戰國時代是農業文明,耕作和糧產是最重要的土地利用,以一級產業為物質生產基礎,而在其大地上,中國人建立邦國的王城和國土之境的農村鄉社,由孟子對梁惠王的對策內容可知,其時魏國有耕耨的農田、自然環境中的湖泊池塘以及仍然自然原始的山林,魏國人民在農田耕作,入山林採樵伐木,在湖塘中捕撈魚蝦;孟子告訴梁惠王只要保護環境生態並且配合四季時節規律來進行農業文明的經濟生活,國家就能健全永續發展,此是王道的開端,而若能實踐「井田制度」,使百姓皆有基本的農舍和田畝,於其中種桑、耕種、豢養,如此,國人就能富足,而進一步就要發展實踐倫理道德的國民教育,使國人皆為孝悌有教化的人民,這就是王道的踐履,由此甚至可以普施王道仁政於全中國。
現代早已是工商業世界,人地關係,已由一級產業為主而轉變為二、三級產業為主而一級產業為輔,在一級產業之中,農林漁牧礦業其實也被二級產業的人員、工具以及現代工業生產物摻入影響支配。環境生態之永續性的如何維護保育,已更複雜,遠非孟子他們那個時代的古人可以想像的。但是依據當代「環境生態學」的知識和科技,只要認真實行環境生態維護保育,依然是可以作到的。最令人憂心者乃在於「現代資本掠奪主義」之貪婪和冷酷,卻常常背道而馳,立乎執政者的地位和權勢,卻為了特權的集體私利而嚴重甚而徹底違逆生態律則,一路毀壞了人類賴以生存永續的自然環境,今之臺灣民進黨亂搞風電、火力發電、在良田、魚塭、公園、綠地上面大肆「種電」,且又破壞海岸環境生態搞天然氣海上接引的管線,凡此種種都是逆天違道的極端惡行,必須予以推翻,否則生態環境一旦被毀壞、污染,一萬年十萬年、百千萬年都無法復初。
寫於 臺北‧天何言齋 2024.03.29 青年節
【奉元問學之三】三國雜談:論曹操
文/尹建維
編按:本文作者尹建維老師為奉元門下弟子,奉元學會創始期會員,長年旅居海外宣講並弘揚夏學。尹老師曾分別於 2018(演講介紹、直播)、2019(演講介紹、直播)年應臺大奉元社邀請進行「智仁勇」專題的系列演講,於去年(2024)年底應邀於學會完成該專題的最後一講(演講介紹、直播),頗受好評!本文為尹老師評論三國時期最具爭議性的人物——曹操。文中基於史實進行深刻地思考與剖析,頗有啟發性!本刊特別徵得尹老師同意轉載,以饗讀者!
******
曹操是三國時代一個主要的人物,議論甚多。事實上,曹操可能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被討論、被引用最多的人物。看易中天的《品三國》,談論曹操也不少。易中天是蠻有些看法,但世間本是各有所長、本無十全十美,若能把曹操談得更剔透一點,應該可以給同學更好的借鑒與學習。
曹操是一個很實際的人,這大家都可能知道。其實曹操還是一個頗為真情的人。問題是真情的人怎麼還會這麼狠?另外的兩個癥結在:曹操是雄,但是不是奸?曹操有沒有理想?
首先,曹操人其實很誠實,感情也真。所以曹操的詩詞才好,他說的很多話才耐人尋味。人太虛偽,不夠真,說些冠冕堂皇的話,沒人聽的。王莽的虛假,根本講不出有味道的話。司馬光頑固不真,他也說不出有味道的話,他寫的東西再多,沒人看的。只要情真,就是好文。如果曹操不處在政治、戰爭的混亂年代,他就是一個會令很多人喜愛的文人。許劭說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確有見地。在亂世,不有本事,怎能存活。劉備不就活得很假,諸葛亮不也活得很累,孫權晚年的殘暴,不也是年輕時候的憋屈?曹操才是活得最痛快的一生。讓人誤會、讓千年來的人指指點點,曹操活著的時候就不介意,死後還會在意?倒是不以曹操為然的人,自己顯得小氣罷了。
問大家一個問題:孫權也算得上是雄,但是不是奸?如果孫權跟劉備一樣,都可稱為是雄,但一般沒有人稱他們為奸。如果他們不奸,尤其是如果孫權算不得奸,那曹操也就不奸。孫權晚年冤殺不少功臣,殺有功的人、殺親近的人比曹操多,但是曹操的惡名高於孫權,為什麼?歷史上的皇帝、英雄、梟雄都屈殺不少人,但曹操的殺,人家就會覺得是故意的、是奸。除了上千年的錯誤、固化的印象以外,也可能因為曹操多智,大家認為曹操不應該會認不清人而屈殺。但是歷史上的皇帝、英雄、梟雄也有許多因為情緒而殺人的皇帝,像漢武帝、唐太宗、朱元璋等等,但好像是曹操就不行、就是奸,為什麼?這不是不公平嗎?似乎歷史上對曹操特別求全責備,這是很有趣的題目。有趣之處可能就是因為曹操太誠實、說真話而造成的。曹操根本不在乎人家對他的印象與評論,他殺了人也不解釋、從不虛情假意。過去,聽一位法師開玩笑地說過,一般信徒是「聽騙不聽勸」,真有點道理。一般人是喜歡假,不喜歡真,因為自己假,對任何真實就都起疑心。
曹操是很可愛的一個人,他經常就說真話。他的《讓縣自明本志令》就是非常真實的大實話,陳述自己從年輕到 56 歲的發展與心理過程。明白地說,曹操是說了他自己並無志向,是一步步的發展,讓他心越來越大,最後大到他自己說:
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因此,他自認是他幫國家撐住了一片天。到了曹操死前一年(西元 219 年),孫權上表勸進曹操稱帝,群臣也勸進。曹操說:「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曹操於是只說了:
若天命在吾,吾願為周文王矣!
我認為曹操完全說了大實話。很多人猜測曹操這個、那個的心思,我認為就是那些人多心,不懂曹操。在政治、軍事場合用計、用謀,不說真話,那是當然的。但是在任何其他不需要說謊的場合,他那梟雄的性格,根本是不屑說謊的。一個人也必須自信、高傲到一個程度,才能了解曹操這種心理的。毛澤東在敵人面前會沒有陰謀嗎?但是,他會覺得陽謀更痛快、更過癮!「怎麼地?我就跟你耍陽謀,我明著讓你看牌,你也玩不過我!」拿破崙不也自取皇冠戴頭上?他需要人家加冕嗎?天下是他打下來的,不是上帝給的。他根本就不相信有人可以代表上帝!我甚至判斷曹操稱公、稱王,是為了下面抬轎子的群臣,滿足他們的一些盼頭。
曹操是個熱血青年。但是曹操並沒有志向。志向這東西太不實際了。走一步、看一步、做一步是最實際的。解決目前問題,比解決未來的問題重要多了。易中天說曹丕接受陳群的「九品中正制」,是同意了士族地主的要求,士族們才支持曹丕坐上皇帝之位的。易中天有一個特別的見地:周朝是諸侯、大夫佔據天下資源。秦漢則是從周朝世襲諸侯大夫的壟斷天下資源,變成了貴族地主的壟斷,因為沒有世襲的諸侯和大夫了;接著再過渡到魏晉南北朝的士族地主的壟斷;隋唐以後,再變成了庶族地主的壟斷。我們暫且接受這個說法,但在曹操手中,陳群等人是無法跟曹操討價還價的。連陳群等勸進皇帝,曹操都不肯,曹操時代,就是法治,同時用人唯才。這些方面,曹操就是「能」,非常實際,毫無玄虛,還很霸氣。這些,曹操一點都不奸,還很實在!說曹丕是接受了陳群等士人的交換,我還沒被說服,但是曹丕比不上曹操的大氣是顯而易見的。
曹操有沒有理想?我認為,曹操有熱情,但沒理想。前面說了,如此實際的人,不會為虛無縹緲的理想而奮鬥的。前面說到的《自述令》等等的故事,曹操自己已經承認了他就是「水漲船高」,野心是一步一步越來越大的,沒什麼理想。什麼理想不理想?皇帝都不想當,還有什麼比這更實際的?熱血沸騰,都是當下。有熱血,還有理想,那種熱情就需要非常充分了,否則支持不了那麼久的。或者這麼說吧:有熱情,還有理想,經常就不容易實際,非常可能一輩子活在虛幻的理想中。有熱情、有理想、還能實際,這是非常非常難得的素質!
說起來,老子似乎是不讚成虛幻的志向的。所以老子說:
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若是這麼說,曹操又實在、又誠實,豈非老子所描述的理想道人?分明不是。問題在哪裡?
依我看,曹操、劉備、孫權後來都犯了一個大毛病:自滿,不求上進了。孫權在稱帝以前,還是很謹慎小心、也很謙虛的。稱帝以後,殺張昭,逼死陸遜,殺了太子、和另一位爭權的魯王。根本就成了暴君似的。劉備赤壁之戰後,就似乎有意冷凍諸葛亮。進益州帶鳳雛,打漢中用法正,連夷陵之戰諸葛亮連進諫的空間都沒有。在夷陵之敗後,諸葛亮感歎:「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劉備不太信任諸葛亮,他插不上話可知。諸葛亮與趙雲這等正直的人不用,信任背主求榮的法正,我對劉備是有很大的疑問的。這樣的劉備,期待他能怎麼上進是不可能的。曹操在進魏公之後,似乎也漸漸喪失上進心。說天下形勢底定,難有大作為或許是。但也未見特別地勵精圖治。不能日新又新,不進則退。曹操到底是英雄垂垂老矣!
曹操是一個蠻可愛的人。他非常誠實,能不騙人的地方,他就都說實話。他有十足的自信,因此,他也不怕自曝其短。《自述令》是大實話。不想當皇帝,最多作文王也是實話。「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也是實話。錯了就認錯。雖然打勝了烏桓,但是勝得太險,因此戰後獎賞當初諫止他伐烏桓的臣子。愛漂亮女人,每次戰勝,都找漂亮女人,本來答應了關羽,把關羽看上的呂布手下將領的妻子賞給他。但在自己看到美女後,卻反悔了,自己收納了。有人說這是關羽千里走單騎去找劉備的原因之一。但是,這說明了曹操不會為面子與承諾傷害自己的感情。曹操是絕對忠於自己的!這豈不是背信棄義嗎?這能不能算是「尾生之信」?自己喜愛,為了一句話,違背自己的意願,對嗎?我了解:信就是信,答應了就別反悔。我也了解:真就是真,真愛美人,需要隱藏嗎?我相信所有的女人都希望遇見曹操這種敢愛敢恨,敢為她不顧一切的,是不是?這之間的灰色是非,不正是千年來,人們詬病曹操之處?但是,曹操就一無所取?曹操這點不很真實嗎?張繡投降,曹操看到他嬸嬸長得漂亮,也收下了,結果張繡叛變,最喜歡的兒子曹昂被殺,大將典韋被殺,遭到太太丁夫人的不諒解。曹操低頭跟丁夫人賠罪,丁夫人不理。曹操也只有摸摸鼻子,灰溜溜地離開。只到了晚年臨死之前,怕到九泉之下見兒子曹昂跟他要媽媽。就是這麼一個除了多智、多才,還任性,真性情、又霸氣的人,不令人生羨、不可愛嗎?但就可惜晚年不求上進,終至實際而不真實,或者說,真實而不純!
有人必然會問:真實有什麼好處?曹操這樣不就很痛快了?這是沒錯,曹操一輩子忙得大約沒時間煩惱,但是,他必然還是有不少煩惱。我認為聖醫華佗在他身側,卻醫不好他的偏頭痛,就說明了他必然有某些心理上的障礙遭致這偏頭痛的問題。結果他另一位最愛的兒子曹沖,就因為華佗被他殺而無法得到適當的醫治而死,會不痛心、不傷心、不煩嗎?主要的,這關係到我認為人生一遭最重要的意義和目的,就是認識自己、發現自己、實踐自己、圓滿自己。這些,都需要有蠻高度的真實才可能做到的。在事功上,曹操有他的成就。但在生命上,他依舊是滄海一粟,歷史過客,人前光鮮亮麗,人後一樣是煩惱無限、難以自控,依舊是不圓滿。否則,曹操怎麼會殺華佗呢?
人生,有光鮮亮麗的一面,有不為人知的一面,這些都不重要。歷史的事功,是人們經常熱衷討論的話題。但是,以成敗論英雄是站不住腳的,以事功論生命也是站不住腳的,以圓滿論生命也是頗為唯心,很多人難以了解,也就難以接受的。外王的事功與智慧,與內聖的圓滿與智慧是不同的。任何人的生命都有事,藉事練心是每個人不論智愚賢不肖都會面臨的事情。也就都是每個人無可避免的「天命」:藉事練心,藉事認識自己、發現自己、實踐自己、圓滿自己。雖然生命的圓滿很不容易界定與討論,但是,不從生命的圓滿來看生命,只討論外王的成就,是永遠沒有滿意的結論的,因為每個人聰明才智、福報因緣、時代不同,沒有主觀的圓滿參與,是無法得出結論的。圓滿生命才是最有價值、最值得追求的。不論事功,只論圓滿,更論真實。曹操的實際,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對象。曹操之後的不務進取,是我們應該警惕的例子。歷史人物留下所有客觀的資料,都需要有我們主觀的認識與判斷,能够讓自己學習與成長才有意義。
尹建維 20250124 洛杉磯
【奉元問學之三】王船山《讀四書大全說》「致中和」在「人道自立」的「日生日成」
文/陳有志
(一)
王船山《讀四書大全說》的目的,在對朱子四書學理的繼承及重建。也是「六經責我開生面」的船山,開啟了「元」為「推善之所自生」,在「成性凝命」的「人道自立」與「日生日成」的「道器無易體」。
《讀四書大全說》所以借胡廣編纂《四書大全》進行重建,其中有兩個批判及一個新面向。批判一,是對朱子《四書章句集注》及其門人,尤其新安學派的詮釋,代表官學影響科舉遺禍的清理。其二,將朱子道學重在天命性理,主張「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為「性、命、情」的分解,在「大中至正,而盡乎人性之良能」,回歸「誠明之心」作為安行利行的實踐,所謂「生知者,誠明也。安行者,至誠也。學知者,明誠也。利行者,誠之為貴也。」
因此,對朱子四書學的重建,主要的任務在修正朱子「致知」在「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轉向「凡仁義禮智兼說處,言性之四德。『知』字,大端在『是非』上說。」即是,把朱子以《大學》「格物」作為《四書》始教,將此重心回歸《中庸》「未發」的「心法」。
《四書大全》是胡廣根據倪士毅《四書輯釋》為底本,擴大纂修為《四書大全》,引用先儒,以朱熹為主,共一百零六人的論述,代表朱熹的新安理學,如陳淳、黃榦、胡一桂、胡炳文、趙汸等,成為明代官學的思想。
船山的批判可謂思維犀利,立場鮮明。本書《大學序》的一開始,馬上對胡炳明(雪峰)解釋朱子「致知」為「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宰萬物」指為「大妄」。如此釋朱子「『義』曰『心之制,事之宜』,豈非以『宰萬物』者乎?釋『禮』曰『天理之節文』,豈非以『妙眾理』者乎?」不就是對「仁義禮智」的不解。
對「仁義禮智」的不解,就是對《四書》的不解。船山立場如此鮮明,正在《讀四書大全說》全書,就在為了繼承及重建《大學章句序》的「仁義禮智之性」,為朱子說的「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大學為大全者。
避免「仁義禮智之性」在「心者,人之知覺」的「應萬事」,成為「妙眾理,宰萬物」,船山將「仁義禮智之性」,修正為「仁義禮智根於心」,所以說「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未發者喜怒哀樂耳。故程子曰:『中者,在中之謂』。」成為《讀四書大全說》的批判,就是為了重建「仁義禮智之性」。重建中最重要的義理關鍵,在朱子「致知」為「所知無不盡」,轉回「言性之四德(仁義禮智)。『知』字,大端在『是非』上說」,致力在《中庸》「致中和」的「自誠」為的性德之教。
總結朱子「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氣形理一,在船山則是以「陰陽一實」及「體用一源」,相應在程頤的道心與人心,扭轉天道為仁義禮智的性,回歸人道的仁義禮智的心。這是自立在人道,顯發「自誠明」的心體,被限定在「陰陽未體」為「兩端一致」的心用。
所以,船山說《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是儒者第⼀難透底關」,又「不可以私智索,⽽亦不可執前⼈之⼀⾔,遂謂其然,⽽偷以爲安。」《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作為「允執厥中」,所以能達天下之德的道學,不能靠自己的想像,也不能僅守一家之說解。就不難理解「讀」《四書》,不可「私智」及「執前⼈」,四書學理也不能為新安學的私囊。
這也是《讀四書大全說》重新探索朱子揭示《大學》引《書經》的「顧諟天之明命」,與《中庸》的「天命」,在明德正心的「明命」與未發已發的「天命」,為何在《中庸章句序》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指出「允執厥中」的「心」,有人心及道心的不同?又「性命」與「心」,有何關聯?
也就是人心,朱子說是「飢飽寒燠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形體,而他人無與焉,所謂私也」,存在人心與道心為「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慾之私矣。」這裡關聯「不知所以治之」的人心,如何發現道心?又如何說「仁義禮智」的「性」,就是道心?
在朱子,「心者,人之知覺」,當接受「天命」的知覺,就把「氣稟所拘,人欲所蔽」的知覺,才轉化成「虛靈知覺」的道心。這是《大學章句》朱子的解釋: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
指出: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身而應事物者也。
另在《中庸章句》指:
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
「具眾理而應萬事」就是「虛靈知覺」的道心,不具眾理的知覺,所應於萬物,只能是血氣形體的人心。只有「虛靈知覺」才可以排除「氣稟所拘,人欲所蔽」,所以有了「人心」與「道心」的不同,「天命」的性,作為「仁義禮智」的眾理,就是「仁義禮智之性」,是導致「道心」的來源。
所以《大學章句》天賦予我的德性,就是章句義理指出「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在《中庸章句》「天命之謂性」,就是: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這是朱子四書學理的精神核心,章句「天命」的性理,指出「天之所以與我」的德性來源。並在《中庸》「已發未發」,特重在「未發」的靜涵中解釋「中和」,即是《中庸章句》說的: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
這個「未發」為靜涵的特徵,就在《答張欽夫》指出「中和」的知覺運用,說:
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
船山對此「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心之所用的天命感通,在整體意義,天命與知覺,就成一個潛在天道作為條件。問題在「虛靈知覺」的心,作為「天命的性」,不就喪失一個自發性的「自立」?
作為血氣形體的人心,如何能產生道心?這個「自明誠」的「教」,不也就只能成為被動?正是船山把「虛靈知覺」,在《讀四書大全說》首要重新詮解為「隨見別白曰知,觸心警悟曰覺」的自明自發,就落在「致中和」為「執其兩端」,在人心與道心的「兩端一致」,指「天命」是一種自發的「時中」。
這是關係《中庸》致中和,為「慎獨」能以「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為「行之者一也」,「其知之,一也」。「其成功,一也。」就是「允執厥中」的精一,朱子所謂「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在「雜於方寸之間」,朱子是「氣形理」被動形上學的精一,在船山則在「神氣形」為主動自覺的精一,主動自覺就是以「人道自立」,在「日生日成」為至誠的本體論。
所以本體的「心法」,就是在兩個批判下的繼承,成為一個新面向的重建,所在「來者以立體,往者以待用」,以「時之所趣,道之所麗」的立體致用,就是《中庸》說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的「時中」。將《大學》轉向《中庸》,以中和詮釋致知,指出「《中庸》說人道章,更不從天論起,義例甚明」,又說「《中庸》一部書,大綱在用上說」。重在人道為用的《中庸》詮釋,成為船山主張「乾坤並建之實,為人道之所自立」,指「陰陽者,二物未體之名」的「用以備體」說。
(二)
朱子《四書章句集註》最爭議的問題,在以《大學》的「格物」關聯《中庸》的「天命」,及指「心的知覺」,在「允執厥中」,成為不偏不倚的道心。最具代表朱子的立場,在《答張欽夫》說的「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這樣「寂然不動」的心,不就是成了一面反射的鏡子,心不是作用者,只是承受者。
「道義全具,其所謂『中』」,以寂然不動的「心」,中和在天命為體用,心呼應了「具眾理而應萬事」,所以「格物」就有「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的致中和。這樣「推極吾之知識」,在承受的心,就不知根據那種知覺起了推動的作用力?
相對朱子「仁義理智之性」的形上性理,船山的修正則在「仁義理智之心」的本體性命。維持同樣相應在《大學》「格物」與《中庸》「天命」,但指「《大學》固以格物為始教,而經文具曰『以修身為本』,不曰『格物』為本」,其次把《中庸》「天命」在「未發已發」,只是誠明之心的體用相涵,為「誠明相資以為體,知行相資以為用」。
同樣,最代表船山重新整合「格物」及「天命」的觀點,具在《禮記章句》卷四十二說的:
格物為始教而為至善之全體,非朱子之言也,經之意也。蓋嘗論之,何以謂之德?行焉而得之謂也。何以謂之善?處焉而宜之謂也。何以謂之至善?皆得咸宜之謂也。不行胡得?不處胡宜?則君子之所謂知者,吾心喜怒哀樂之節,萬物是非得失之幾,誠明於心而不昧之謂爾,非君子之有異教也。人之所以為人,不能離乎君民親友以為道,則亦不能捨夫人官物曲以盡道,其固然也。今使絕物而始靜焉,捨天下之惡而不取天下之善,墮其志,息其意,外其身,於是而洞洞焉,晃晃焉,若有一澄澈之境置吾心而偷以安。
指出「知」只是「吾心喜怒哀樂之節」,格物在「誠明於心」對應著「萬物是非得失之幾」,「喜怒哀樂之節」的未發已發,只在知節是非,行處於「至善」,所以才有了「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就是「喜怒哀樂之節」,即是「心」所「處焉而宜之」的「至善」。
又同樣代表船山對朱子指《中庸》的「未發已發」為體用主張的修正,見在《讀四書大全說卷二·中庸》說:
天下之理統於一中。合仁、義、禮、知而一中也,析仁、義、禮、知而一中也。合者不雜,猶兩儀五行、乾男坤女統於一太極而不亂也。離者不孤,猶五行男女之各為一〇,而實與太極之〇無有異也。審此,則「中和」之中,與「時中」之中,均一而無二矣。朱子既為分而兩存之,又為合而貫通之,是已。然其專以中和之中為體則可,而專以時中之中為用,則所未安。
指朱子《中庸章句》說「『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執中」為「已發」就是「分而兩存之」的「體用二分」,所以「專以『時中』之『中』為『用』,則所未安」,是對朱子在「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認為朱子的不充分。
《讀四書大全說》解釋《中庸》的篇名及篇意,稱「中者體也,庸者用也」,意義在「性道,中也;教,庸也。修道之謂教,是庸皆用中而用,用中為庸而即以體為用」,「即以體為用」正是船山「體用一源」、「體用相因」,指出「陰陽者,二物未體之名」在「立兩以見一」為「用以備體」。道在人心,因人體道,不是因神道而設教。
這是船山一面繼承朱子《大學》「格物」同步《中庸》「天命」,指「心的知覺」在「允執厥中」的不偏不倚,另一面對《中庸章句》「未發已發」為「體用」的修正。這個修正將朱子視「中和」為「體」,「時中」為「用」的二分,指體用不是知解或涵養一個體,才能知解如何為用。應該只是即體為仁,即用為道。所以,他進一步解釋「未發已發」為「第⼀難透底關」的詮釋,只在把「未發」的體與「已發」的用,兩者視同一物,為「體用相因」、「體用相涵」。
朱子這種項式拆解,作為分解的二分形態 ,不只見於《中庸章句》「體用」二分,同樣在《大學章句》也把「物格而后知致」分為兩段,即把「格」成為「知」的條件,「格」作為「虛靈之心」的知,為了區別「氣質之心」的習。故朱子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都是心,不成只道心是心,人心不是心。」所以「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知」就成為擴充經驗知識的「識」。
船山認為這正是「若分言之,則『格物』之成功為『物格』,『物格而後知至』,中間有三轉折。藉令概而為一,則廉級不清,竟云『格物則知自至』,竟刪抹下『致』字,一段工夫矣。」致知只是「知是非」的道德工夫。項式拆解,就是「藉令概而為一,則廉級不清」,因為過於支離破碎,最終無法理解「致」,何以為「一」,作為工夫的本義。
朱子四書學理,所以落入體用二分、知至二行的關鍵,船山認為就在「天命」起源於「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為理氣合一的解釋。朱子將「心性情」分解為「性是未發,情是已發」,船山則維持「中為性」的「體」,所以為「心為已發,性為未發」都是「用」。
將「心性情」分解,作為「性是未發,情是已發」的解釋,起源《中庸章句》「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船山指朱子「命,猶令也」,本於董仲舒 「天令之謂命」 。朱子及其後學的解釋,如陳淳說 「『分付命令他』,讀『令』如『零』,便⼤差謬。⼈之所性,皆天使令之,⼈其如傀儡,⽽天其如提彄者乎?」這樣人不就是成了天的傀儡,一種機械論。
這是船山對朱子四書學理,沉浸在天道天理的批判。船山認為「令者,政令,如⽉令、軍令之謂,初不因命此⼈此物⽽設,然⽽⼈受之以爲命矣。」「令」為「⼈受之以爲命」,就是「任命」、「委任」或「賦予」,是承體授用的委任及代理的意思。
船山「令」為「⼈受之以爲命」,是根據孟子的「所性」,意義在《中庸》「取人以身」的「仁者,人也」,即他說:
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取人以身」的「所性」,就在船山《禮記章句》解釋為「備仁之理於身」,也就是「仁者,人也」,為「人道自立」。所以說的「所性」,就是船山重詮「虛靈知覺」,指的是「隨見別白曰知,觸心警悟曰覺」。指:
隨見別白,則當然者可以名言矣。觸心警悟,則所以然者微喻於己,即不能名言而已自了矣。知者,本末具鑒也。覺者,如痛癢之自省也。知或疏而覺則必親,覺者隱而知則能顯。趙格庵(趙順孫)但據知覺之成效為言耳,於義未盡。
知覺成效的識,無法擔負「取人以身」的觸心警悟。「覺則必親,知則能顯」必親為「喜怒哀樂之節」就是「禮」,能顯為知的體用就是「義」,所以「仁義禮智」之心,為知覺是指人道為本體的心,不是形上為明令的識。
觸心警悟的能喻能言,就在自身擁有知覺本體,所以說為「所性」,因能「取人以身」,能「痛癢自省」,這才是「虛靈知覺」的全體大用。船山說:
所性之幾發於不容已者,於人之所當知者而先知之,於人之所當覺者而先覺之,通其志,成其務。
也就是在: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未發者喜怒哀樂耳。故程子曰:「中者,在中之謂。」
這是《讀四書大全說》對朱子四書學的繼承及重建。就在綜合《大學》「正心誠意」與《中庸》「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的天道性命。整個重心就在「天命」及「未發」重新修正。將朱子的天道授命的體用,轉為所性為節的自覺,為本體論體用,指出「取人以身」只在「通志成務」。
所以《讀四書大全說卷二·中庸》又說:
但言體,其為必有用者可知(言未發則必有發)。而但言用,則不足以見體。(時中之中,何者為體耶?)時中之中,非但用也。中,體也;時而措之,然後其為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體也;發而皆中節,亦不得謂之非體也。所以然者,喜自有喜之體,怒自有怒之體,哀樂自有哀樂之體。喜而賞,怒而刑,哀而喪,樂而樂。則用也。雖然,賞亦自有賞之體,刑亦自有刑之體,喪亦自有喪之體,樂亦自有樂之體,是亦終不離乎體也。《書》曰:「允執厥中」。中,體也;執中而後用也。子曰:「君子而時中。」又曰:「用其中於民。」中皆體也;時措之喜怒哀樂之閒,而用之於民者,則用也。
(三)
最後關係船山「推善之所自生」為「元」,把形上性理,轉為本體道器,所在「成性凝命」的「人道自立」及「日生日成」的「道器無易體」,也是關於船山「乾坤並建」與理氣道器「成兩間之大用」的理解。
船山以「誠明相資以為體,知行相資以為用」,指天命的體用,是代理委任的「順代天功」,為主動的總攬承擔,來替代朱子《中庸或問》「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視「天命」為號令,一種條件限制成的被動。同時,把朱子「虛靈知覺」的心,詮釋為「誠明於心」。這是《讀四書大全說》指出「隨見別白曰知,觸心警悟曰覺」的「知覺」,以明白警悟的「自誠明」為自明的心。所以「未發已發」在「喜怒哀樂之節,萬物是非得失之幾」在「誠明於心而不昧之謂爾」。
這是船山以「誠明於心」為體用根據的兩大立場,對朱子四書學理的修正。他認為「致中和」作為「繼天立極」的道學,中和只能指人透過兩間辯證的警悟知覺,建立在「成性存存」為世間的人道,故說「《中庸》說人道章,更不從天論起,義例甚明。」「天道」以陰陽為兩間,如「人道」以男女為兩間,但作為人道的知覺,就顯見在道器之間,所以「據器⽽道存,離器⽽道毀」,知覺警悟了道器之間的一切現象。
理解船山「陰陽一實」的現象,如「至誠之道,一實不歉,便是中行」為「中行」的含義,就在感覺現象只算是被動的確定性,另有一層存在兩間被辯證為主動知覺的確定性,所以「合之則為太極,分之則謂之陰陽。不可強同而不相悖害,謂之太和,皆以言乎陰陽靜存之體,而動發亦不失也。然陰陽充滿乎兩間,而盈天地之間惟陰陽而已矣。」分合只存在主動辯證的知覺。
這是《中庸》「天命之謂性」稱揚的「性」,只能存在辯證知覺所確定的道心,「性」為道心的起源,如同現象為被動的感覺就存在人心的起源。故說「兩間之大,一物之體性,一事之功能,無有陰而無陽,無有陽而無陰,無有地而無天,無有天而無地」,又「陰陽之變化為兩間必有之理數」,所以「繼善成性」以「唯心不足以盡性,而非性不足以凝道」。
所以「順代天工」,只能從辯證知覺的「用」找到辯證自然的「體」,因為觸動「體」的「知覺」,在知覺「兩端一致」的「中和」,成就《中庸》「人道敏政」的知人之道。知人者能「用其中於民」,以「通志成務」。
從「用」找到「體」的「知覺」觸動,也就是辯證知覺所確定出人心道心的一致,就在「加物」成為「我」的自我辯證。船山解釋說「我者,以己加物之稱」,也是「推者,舉心加物之謂也」。「兩端」為「合二以一者,既分一為二之所固有」,「加物」為「合二以一」,而「二之所固有」,為一者合,為二者仇。因此,二者固有,一者加合,故稱「兩端一致」,為「繼善成性」的「日生日成」。
船山《讀四書大全說》以人心中和的「知覺」為「仁義禮智」,如同《周易內外傳》以天心的自然「象數」為「元亨利貞」,兩者為兩間都存在氣機自然之感的「盈於兩間」。「盈於兩間」的「合二以一」起源,就在「加物」的「我」所能把固有的二,合一在「兩端一致」。沒有「我」的辯證,就沒有「日生」的天道,以及「日成」的人道。
這是自然現象提供有限現象感覺的人心,透過知覺發生在對立面的自我轉變的統一,根據這個轉變成為「我」的道心,作為實體的本性。當所有的二為一,就是《中庸》「仁者,人也」,在船山詮釋為「我」。所以,「加物」為警悟的知覺,就在這個實體有個「加」作為誠意的心,所以說「君子誠意。誠意者,實其意也,實體之之謂也。」
即此,沒有「我」的心,就是人心為「固有的二」的私心,有「我」為「加物」的心,這是朱子所稱「道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船山進一步揭示道義之心的公共自然,「斷制者」就在「二氣之動,交感而生,凝滯而成物我之萬象,雖即太和不容已之大用,而與本體之虛湛異矣。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加物」為「二」,「合二以一」為「兩端一致」,「加」就是「通志」。「加」不是隨機的相遇相加,「加」在合「義」,為「益物而合義之謂」,是「太和不容已之大用」,對立中有一個「理義」統一。如「盈於兩間」的天道與人道,天道的自然,不只是自然現象,「天無定體」只有「象數之自然」,成為「渾然一環」,又指「物之自然,非我言之,非我事之,我亦繇焉而不知。」
「天無定體」為「物之自然,非我言之」的不知,但在「加物」為我,是我所知的道心。船山指沒有辯證性的知覺,就沒有「合二以一」為「兩端一致」的統一事理。這是「陰陽者,二物未體之名」,在「立兩以見一」,才有「體用相涵」找到「物我一原」的「渾然一環」。所以「一環圜合而兩環交運」的人道與天道,也在「合二以一」統一,找到生成的意思在圜合交運的「二氣之動,交感而生,凝滯而成物我之萬象」
沒有辯證人性,就沒有道器的世間,疏忽知覺可加物的形而下的真實世界,也就疏忽天道之性。「兩環交運」為多重「兩間」,指所有平行對立的自然,在「合二以一」的辯證下的知覺,才能揭示「體用相涵」的「物我一原」,統一形上與形下的兩間,也統一了物我的兩物,為「統此一物,形而上則謂之道,形而下則謂之器,無非一陰一陽之和而成,盡器則道在其中矣。」
起源於「加物」的知覺,在「象,數,道,氣,時,物,器」,作為一切辯證範疇中,氣為變化、象為氣的結果、數為象的生成及增成、道為器物的整體、時為有限及無限的圜合、物為外部現象、器為審量成務,等等思辨。
自我否定才有思辨物我統一的肯定,顯見在「象,數,道,氣,時,物,器」,也就是兩端的「一」與「二」因為加物,在「對必反其為」,確立了「兩端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也。」牽動知覺的象數,起因「知覺運動之氣」。故說「無心之動,終合揆於兩儀之象數,為萬物之始,皆陰陽之撰(規律)」。
船山說「一體者為圓,為天道。屈伸順感而各得,神之圓也。不倚於形器,則不徇物而流。」「一體為圓」,正是警悟知覺揭示「日生日成」的循環辯證,天不倚於形器,但人道就必須有一種形器辯證的結果,以及隨著世界不繼循環的重複變化。所以「象數」自然的「日生」為二,成分化的多,在「加物」盡器的「日成」,為一,成整合一體。
這種差異交感的相互循環,船山以《周易》「象數」的自然辯證,就在三陰三陽,象徵流變交感的循環辯證,指:
太極,大圓者也,圖但象其一面,而三陰、三陽具焉。其所不能寫於圖中者,亦有三陰、三陽,則六陰、六陽具足矣。特圖但顯三畫卦之象,而《易》之《乾》《坤》並建,則以顯六畫卦之理。
表現在: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加物」的知覺辯證,能同步於陰陽變化的現象辯證,呈現在兩間為多重的「兩端一致」,所以現象以陰陽確立一個天道,為「陰陽者,定體也,確然頹然為二物而不可易者也。而陰變陽合,交相感以成天下之亹亹者,存乎相易之大用。」而知覺以加物中和則為人道,就是「人之立己處人,兩端而已矣」。
無器不成道,無器不成體,器是精神及制物的載體。首先必然反映在器用現象中被賦予節文世界的秩序。只有這種微觀心智,才理解知覺的體知察覺了人文人道世界,如何賦予或擁有形體及形體秩序的構成。這是個體知覺在加物中攫取一個共存,反映成了一種道器的創造。
「順代天工」為「兩端一致」的中和知覺,就是「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及「斷天下之疑」的一種現實歷史。這是船山道器思想,就在「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所以說「象者氣之始,居乎未有務之先;數者時之會,居乎方有務之際。」氣有象數為知覺,成為「制器尚象」,就當有一個歷史為氣始時會的開物成務,所以說「『象⽇⽣』⽽為載道之『器』,『數成務』⽽因⾏道之『時』」。
「兩間」辯證,超越了兩漢到宋明的思維範疇,可謂「六經責我開生面」的景勝。《讀四書大全說》代表儒家思想,從兩漢天人感應,到何晏《語論集解》「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為任性任道的玄學詮釋,轉向宋明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的性理,在船山確立「體用相涵」之說,開啟第四期的新視野。
這也是為熊十力以「中正之應」為廣生,再進一步成了「翕辟成變」的「體用不二」說的源頭。船山「用在體中」的相涵,開啟熊十力「體用不二」之先,兩者是毓老師主「奉元之舉」及「奉元之應」的根源。這也是理解「道器無易體」,在船山所稱「推善之所自生」為「元」,在「立兩以見一」的「人道自立」,將有助探索「奉元之行」的奧質。
【公告事項之一】〔開課預告〕趙中偉老師:乾坤六子,一索得男——「乾坤六子卦」解析
文/秘書處
【公告事項之二】四月行事曆
文/秘書處
